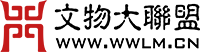——此文为袁学军口述——
—1—
1988年我在解放军画报社,看到成都军区后勤部出过川藏路的画册,觉得应该搞几个专题,就在军画报上做了6期川藏路的连载,和王达军跑了几次川藏线。在这个采访中间我们就想跑西部,我就说我们应该搞个五万里,和达军一拍即合。王达军在成都军区后勤部,川藏路归成都军区后勤部管。那时我和王建军还不熟,是达军提议叫王建军一起去,因为考虑建军开车开得好,修车好,又喜欢摄影。没有任务他们也请不了这么长时间假。我写了报告给画报社,建军找了山鹿汽车厂国产越野车(北京吉普改的)赞助,把事情定了,西部五万里。
西部主要是成都军区、兰州军区管。以军画报的名义搞西部五万里的连载,这样由军区发通知,给我们解决了油票,一路上的吃住基本上在兵站,成都军区一个厂赞助了些羽绒服、鞋。我是军画报记者,这是正式的工作,采访西域卫士,主要跑边防,不是一个盲目的行动。王达军是军区后勤部的名义,建军是我们特别邀请的。建军最早是汽车兵,特别喜欢弄车。这样组成采访小组,“三军”是巧合,后来在路上,大家都说“三军”。
1990年4月4日,“三军”从成都军区大院里出发。
1990年4月4日天气多云汉源县
四四是“是是”的意思,我们选择了这个日子,作为西部五万里出发的日子。
成都军区大院内,主席像前的广场上,由山鹿汽车厂合作的西部行采访开始。山鹿牌汽车装车完毕,军区政治部主任等及摄影界、报社、电视台一起为五万里送行。还有所属厂及企业局领导参加。
9:30,出发。路经成都平原、雅安,晚12点驻汉源县。整车、检修。
王达军、王建军、袁学军此行一路顺利。
第一天兴奋、疲劳伴随,晚上2点还没入睡。考虑如何完成此次采访任务等问题。
——摘自袁学军日记
先跑云南方向,一阶段之后回来成都军区休整一段,搞车(修车),再出发。因为是国产车,不禁跑。带的零件也不多,比如防震的胶皮,跑不了几天就坏了,零件都是王建军换。那时路也不好走。跑一段回来要发稿,因为都是胶片,然后休整几天再出发。这样先后有4次,西部五万里行总共前后7个月,实际行程有7万多里。
—2—
我原来主要是拍人物,很少出去拍风光。那时获金奖的片子也是人物。80年代,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四月影会。1983年我正在人大分校上大学,1986年全国艺术影展获奖《我们劳动去》。那时候属于创作,部队搞新闻,主要发稿给报社,做专题,拍人物风情。当时学习资料非常少,也就是到北京图书馆看书,同学间交流一下。我记得关于风光摄影,当时有李元的讲座,在《大众摄影》、《中国摄影》上登过。吕玲珑拍得也不错。西部风光摄影很少,我拍得也比较盲目。我们画报社记者去西藏拍回一些片子,我看了就觉得真漂亮,从光影角度觉得风光很美。后来跑川藏路,和王达军也拍了些片子,经过二郎山、巴塘、林芝等地,发现地理地貌光线啊都很美,当时就开始拍。我拍风光还是受王达军、王建军的感染,他们俩是最喜欢拍风光的。开车出去一早一晚,觉得好的就拍。五万里之前我对风光没什么特别感觉,就是好奇。走的过程中,他们两个拍也影响了我。一路上我还跟他们争呢,他们说风光好,我说人物好。我说风光现在拍,过几天人家来还能拍,但人物,过去了就过去了。可是我一边争论一边就在拍风光了。没有想系统地去搞,在川藏路上见到好的风景好的光线就拍。
从绿春到健水沟约200公里,但绿春到元阳一带的梯田太美了。位于元阳县城十多公里的哀牢山下的攀枝花村梯田可算得着中国之最。那线条,那起伏的水田,在阳光的折射下,云的阴影部流动的明暗,使新的禾苗变得富有生命。田野中,还有哈尼族、苗族穿戴的农民在辛勤播种。见到如此情景,三军高兴地跳下车,不愿走了。下午4点钟了,几个人在烈日下,人在曝光,梯田也在胶卷上曝光。中午饭也不愿意吃。到大家觉得实在是拍够了的时候,才想起吃了午饭再来赶光线。
在县城的一家小饭馆里,自己洗菜,自己炒菜,吃罢后,安排好住宿,又匆匆赶到拍摄点。
下午6点多,光线正好,色温正好,偏振镜使自然的景色变得更加饱和。梯田之美,光线之美......相机在实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收起。心里还一直怀念着那一片景,一片情。
——摘自袁学军日记
当时军画报胶卷也受限。反转片基本没有。富士柯达就自己买了,黑白的就乐凯,另外在八一厂买了电影胶片。王苗还赞助我们一点胶卷。成都新华摄影之家赞助了一二十个黑白卷。一趟带30个卷左右,很节约。我用的是尼康FM2,F3带马达的,哈苏。
还借了个4×5的,不会用,就学了装片子,片子还放反了,回来冲出来全是红的。也拍些反转片,自己买的,不多,两三盒,跑这么大一圈,就二三十张。王达军带的是玛米亚,也有135。王建军用的是自己买的佳能,好像也借了120的。当时以拍摄报道部队边防为主,那是此次采访的主题。风光是路上见到了就拍,比如看到了云南土林,拍了很多土林图片,途中风景特别好。当时也仅限于一早一晚拍摄,从光影角度拍比较好看的,属于打龙的。
—3—
西部五万里,走过的路。
1990年5月3日阴转雪察隅
......
车在弯弯的公路上慢慢爬行,车一会儿加上一档,才能慢慢冲上去。今天建军一人掌汽车盘子。当车行驶到德姆那山时,雪下得更大,路边的雪墙比车还要高。好一阵雪。我多次要求停车拍照,可建军说,这里不能停车,停下来再走可能就走不动了,在这里不是饿死就得冻死。为了了愿,在一段较高而平的途中,我们还是停下车,拍下了这条天险之路。这是一条从未见过的路。
火焰山太热,那里白天行车的人太少,跑惯了这条路的人都是在晚上通过这里的。本来该住在哈密,可到哈密时才晚上8点,而这里比北京要晚两个小时。太阳10点多才落山,天色才慢慢黑下来,因此,在哈密分区加油后,在一家地方四川饭馆吃了个川菜,填饱了肚皮,准备连夜赶到火焰山。
......
22日晚到23日晨,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奔驰的山鹿车轮声和狂风。这一夜风够大的。车先由我驾驶,晚上车不多,时速80码左右。车外的狂风足有8级,吹得我的手直撑一边,不敢放松。当达军接过我的方向盘时,不但有狂风,紧接着是暴雨,路滑。我们再三强调安全,时速时常提醒,不要超过60码,不要超过50码。建军接车时是最艰困的一段路,不但是风雨的可怕,这时也是人最困倦的时候。我时而给他喝点茶水,说话,有时还哼点小曲。但到了3点钟时,我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梦乡。4点醒来,见建军有点支持不住了,我叫他停下车,哪怕睡上半小时的觉,也就好了。加之风雨使我们车的大灯被损坏,视线不好,绝不要为赶路,稍不注意遇到危险。凌晨4点多时,建军醒来,我本来想开一段时间车,此时,他有点不放心,还是爬起来继续前进。我怕他困,他满怀信心说没事。临赶到火焰山时,达军好像有精神了,接过车,6点多钟到达火焰山下,等日出。这个地方日出要8点,还有两个小时,大家在车上眯了两个小时。在阳光下,大家醒来时,都发现对方的脸色不好看。
的确,大家太困倦,没休息好,没精神,但当见到日出后的火焰山如此壮观时,都精神振奋,拿起相机各自寻找着拍摄点。火焰山自东而西,横亘在吐鲁番盆地中部,为天山支脉之一,形成于五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期。地壳横向运动时留下的无数条褶皱带和大自然的风蚀形成的火焰山起伏的山势和纵横的沟壑。在阳光的强烈照耀下,赤褐砂岩烁烁闪光。
阿里到扎达的路根本不叫路。一路上不知过了多少河,没桥,全靠冲水过去。路呢又全是搓板路,车速根本没办法加快,再说还要爱护车,车如果在路上坏了,几百公里无人那就麻烦了。
走旧公路要100多公里,但是要翻两个大坂,的确够人害怕。这路我不敢驾驶,停下车叫建军来驾驶。路窄不说,全是烂路,还是斜坡路,翻山不见顶,过一道弯,翻一座山,叫人出大把汗。
车不停地使用加力档,吃力地在蜿蜒的山路中盘旋。翻第二道大坂时,天色突变,下起了大雪。已是下午8点多了,建军不想开车了,王达军又接过了方向盘。下山时,他格外紧张。真他妈的比川藏路还烂,这哪叫路啊。
休息时,吃了个西瓜,干粮。实在太饿了,中午那顿稀饭哪能顶得住呢。建军说“肚子的奶油都没了”,达军说“最近严重缺营养”。在高原海拔5000多米的路上,我们三人的心都发慌。
当下山时,雨雪停了,前方看见光线。大家估计会遇上特别的光线,停下来准备拍摄。不一会,果然光线从云彩中射出,大家急忙拿出相机拍摄光影中的雪山。等了一下不够理想,又重新发动车辆继续赶路。车刚下到沟里准备上坡时,突然发现二道彩虹,特别醒目。我们催建军加速冲上坡,好取景。开足了马力,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山头时,彩虹也退了。大伙儿好一阵遗憾。
进入扎达的三岔口分道时,天色慢慢地黑下来了。这里的夜是晚上10点半左右。分道后我们是顺着一条河沟驶向扎达。这里本来有路,可是常年河沟的路被水冲洗,自然就没有路了。加上夜间行车,一会儿就不知道跑到哪条道上去了。基本上是顺着水流的河沟瞎开!
最烂的路还是建军在开,当过一个沟翻一个坎时,两次挂上加力挡,车都歪到很危险的地步,有翻车的可能,不敢再翻了,干脆顺着泥泞的河走。建军出汗了,在河泥里走怕把车陷入泥中,那就没办法了。大家都没走过这种路,建军一急“今晚只有拼了”。开足了马力,在河沟的泥泞中东倒西歪地向前爬行。我们的山鹿车很争气,又一次显示了它的越野性能。不知走了多久,总算是翻出了这条可怕的沟。
当翻上一个坡时,已近半夜1点多钟了,又不知道到扎达的路。继续开吧,大家开玩笑说,不要开到印度去了。这里离国界线已经不远了。达军太困了,几次提出“别走了,今晚就在车上过夜,明天早上再说”,建军坚持要开到扎达县城。
退回来找了一下路,心里没数。看地图也觉该到了,还是往前走吧,沿着河走。当看见一个桥和几个亮着灯的房子,这才心里有数了。
到扎达县已经两点钟了,到武装部叫开了门时,达军已睡着了,走进房子睡觉都不愿意,说了一声“我就睡车上算了”。我和建军什么东西也没拿,进了房子,顾不上室内的藏味,倒上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睡到早上10点,醒来时见窗外阳光很好,照在群山上,群山常年风化,显得特别壮观......有名的“古格王国遗址”就在扎达县境内20公里处......
—4—
高原的路很烂,开车非常危险。建军开得最多,达军也开,我也开,在云南那趟我把车学会了,这也算五万里行收获之一吧。当然,除了采访任务外,这趟下来收获最大的还是风光片子。风光还是靠一早一晚。很多拍摄点都是自己探出来的,要出一个好的风光片很难,有时十天八天也没一个好天。当时还没有从地理地貌啊这些方面去系列反映的概念,是拍多了积累下来慢慢有了思考。开始都没想系列反映中国西部风光问题,总是从景点上,往那里赶,路上遇到光影好的就拍。也没有想出画册,就是想展览,参赛,获奖。当时这就是摄影的出路,再有就是杂志刊登。
回来后,我说要把三军的名号打出去,做影展啊闹一下,对五万里也有个交代。但后来一忙就各干各的了,也没这个精力和经费,影展什么的也没办,但每个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都获了不少奖。
五万里行之后确实风光摄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部回来后,很多奖也就出来了,因为大家一看,很新,从地理从光线都很新。再后来又去几次,就找不到那个感觉了。当时的新鲜感、光线感就不一样了。有些地方反复去了好多次。我从小学美术,构图光影很敏感,一旦拍了风光还是有一定基础的。没有从地理的角度拍,是从审美的角度拍的。回来后画报刊登了边防报道,也刊登了一些风光作品,结合了哨所,使专题生动。1990年,我40岁,精力最旺盛的时候。90年代靠这些片子一年二三十个奖,风光占了不少比例。当时我获得的奖金最高的奖是广东的一个万元奖,一组四张西部片,就是土林、阿里......第一个万元奖。
回来后,我实际上也很苦闷,把万里行的片子拿出来看,疑惑这样的风光到底行不行。记得曾经有人到美国去,我整理了30张图片,让人家带到美国去请外面的人看看。就是想,都拍过了,怎么才能提升。后来人家跟我说我这个风光太讲究光影效果了,读不出什么东西。用光是摄影最基础的东西,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对你拍摄对象的理解。后来想想,我们遇到过很多地理地貌的东西非常感人,石头、树的结构和大自然的关系啊,但当时是不注意的。再后来我去拍,就是去抓拍自己心里对事物的理解,而不是寻找一早一晚了。我现在拍得比较写意一些,上一届全国影展又获金奖,把风光的因素加进印象的东西,最高的境界是印象,不是写实,这也是别人重复不了的。中国的风光也该改变一下,并不一定都要拍很美的那种风光。
—1—
1988年我在解放军画报社,看到成都军区后勤部出过川藏路的画册,觉得应该搞几个专题,就在军画报上做了6期川藏路的连载,和王达军跑了几次川藏线。在这个采访中间我们就想跑西部,我就说我们应该搞个五万里,和达军一拍即合。王达军在成都军区后勤部,川藏路归成都军区后勤部管。那时我和王建军还不熟,是达军提议叫王建军一起去,因为考虑建军开车开得好,修车好,又喜欢摄影。没有任务他们也请不了这么长时间假。我写了报告给画报社,建军找了山鹿汽车厂国产越野车(北京吉普改的)赞助,把事情定了,西部五万里。
西部主要是成都军区、兰州军区管。以军画报的名义搞西部五万里的连载,这样由军区发通知,给我们解决了油票,一路上的吃住基本上在兵站,成都军区一个厂赞助了些羽绒服、鞋。我是军画报记者,这是正式的工作,采访西域卫士,主要跑边防,不是一个盲目的行动。王达军是军区后勤部的名义,建军是我们特别邀请的。建军最早是汽车兵,特别喜欢弄车。这样组成采访小组,“三军”是巧合,后来在路上,大家都说“三军”。
1990年4月4日,“三军”从成都军区大院里出发。
1990年4月4日天气多云汉源县
四四是“是是”的意思,我们选择了这个日子,作为西部五万里出发的日子。
成都军区大院内,主席像前的广场上,由山鹿汽车厂合作的西部行采访开始。山鹿牌汽车装车完毕,军区政治部主任等及摄影界、报社、电视台一起为五万里送行。还有所属厂及企业局领导参加。
9:30,出发。路经成都平原、雅安,晚12点驻汉源县。整车、检修。
王达军、王建军、袁学军此行一路顺利。
第一天兴奋、疲劳伴随,晚上2点还没入睡。考虑如何完成此次采访任务等问题。
——摘自袁学军日记
先跑云南方向,一阶段之后回来成都军区休整一段,搞车(修车),再出发。因为是国产车,不禁跑。带的零件也不多,比如防震的胶皮,跑不了几天就坏了,零件都是王建军换。那时路也不好走。跑一段回来要发稿,因为都是胶片,然后休整几天再出发。这样先后有4次,西部五万里行总共前后7个月,实际行程有7万多里。
—2—
我原来主要是拍人物,很少出去拍风光。那时获金奖的片子也是人物。80年代,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四月影会。1983年我正在人大分校上大学,1986年全国艺术影展获奖《我们劳动去》。那时候属于创作,部队搞新闻,主要发稿给报社,做专题,拍人物风情。当时学习资料非常少,也就是到北京图书馆看书,同学间交流一下。我记得关于风光摄影,当时有李元的讲座,在《大众摄影》、《中国摄影》上登过。吕玲珑拍得也不错。西部风光摄影很少,我拍得也比较盲目。我们画报社记者去西藏拍回一些片子,我看了就觉得真漂亮,从光影角度觉得风光很美。后来跑川藏路,和王达军也拍了些片子,经过二郎山、巴塘、林芝等地,发现地理地貌光线啊都很美,当时就开始拍。我拍风光还是受王达军、王建军的感染,他们俩是最喜欢拍风光的。开车出去一早一晚,觉得好的就拍。五万里之前我对风光没什么特别感觉,就是好奇。走的过程中,他们两个拍也影响了我。一路上我还跟他们争呢,他们说风光好,我说人物好。我说风光现在拍,过几天人家来还能拍,但人物,过去了就过去了。可是我一边争论一边就在拍风光了。没有想系统地去搞,在川藏路上见到好的风景好的光线就拍。
从绿春到健水沟约200公里,但绿春到元阳一带的梯田太美了。位于元阳县城十多公里的哀牢山下的攀枝花村梯田可算得着中国之最。那线条,那起伏的水田,在阳光的折射下,云的阴影部流动的明暗,使新的禾苗变得富有生命。田野中,还有哈尼族、苗族穿戴的农民在辛勤播种。见到如此情景,三军高兴地跳下车,不愿走了。下午4点钟了,几个人在烈日下,人在曝光,梯田也在胶卷上曝光。中午饭也不愿意吃。到大家觉得实在是拍够了的时候,才想起吃了午饭再来赶光线。
在县城的一家小饭馆里,自己洗菜,自己炒菜,吃罢后,安排好住宿,又匆匆赶到拍摄点。
下午6点多,光线正好,色温正好,偏振镜使自然的景色变得更加饱和。梯田之美,光线之美......相机在实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收起。心里还一直怀念着那一片景,一片情。
——摘自袁学军日记
当时军画报胶卷也受限。反转片基本没有。富士柯达就自己买了,黑白的就乐凯,另外在八一厂买了电影胶片。王苗还赞助我们一点胶卷。成都新华摄影之家赞助了一二十个黑白卷。一趟带30个卷左右,很节约。我用的是尼康FM2,F3带马达的,哈苏。
还借了个4×5的,不会用,就学了装片子,片子还放反了,回来冲出来全是红的。也拍些反转片,自己买的,不多,两三盒,跑这么大一圈,就二三十张。王达军带的是玛米亚,也有135。王建军用的是自己买的佳能,好像也借了120的。当时以拍摄报道部队边防为主,那是此次采访的主题。风光是路上见到了就拍,比如看到了云南土林,拍了很多土林图片,途中风景特别好。当时也仅限于一早一晚拍摄,从光影角度拍比较好看的,属于打龙的。
—3—
西部五万里,走过的路。
1990年5月3日阴转雪察隅
......
车在弯弯的公路上慢慢爬行,车一会儿加上一档,才能慢慢冲上去。今天建军一人掌汽车盘子。当车行驶到德姆那山时,雪下得更大,路边的雪墙比车还要高。好一阵雪。我多次要求停车拍照,可建军说,这里不能停车,停下来再走可能就走不动了,在这里不是饿死就得冻死。为了了愿,在一段较高而平的途中,我们还是停下车,拍下了这条天险之路。这是一条从未见过的路。
火焰山太热,那里白天行车的人太少,跑惯了这条路的人都是在晚上通过这里的。本来该住在哈密,可到哈密时才晚上8点,而这里比北京要晚两个小时。太阳10点多才落山,天色才慢慢黑下来,因此,在哈密分区加油后,在一家地方四川饭馆吃了个川菜,填饱了肚皮,准备连夜赶到火焰山。
......
22日晚到23日晨,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奔驰的山鹿车轮声和狂风。这一夜风够大的。车先由我驾驶,晚上车不多,时速80码左右。车外的狂风足有8级,吹得我的手直撑一边,不敢放松。当达军接过我的方向盘时,不但有狂风,紧接着是暴雨,路滑。我们再三强调安全,时速时常提醒,不要超过60码,不要超过50码。建军接车时是最艰困的一段路,不但是风雨的可怕,这时也是人最困倦的时候。我时而给他喝点茶水,说话,有时还哼点小曲。但到了3点钟时,我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梦乡。4点醒来,见建军有点支持不住了,我叫他停下车,哪怕睡上半小时的觉,也就好了。加之风雨使我们车的大灯被损坏,视线不好,绝不要为赶路,稍不注意遇到危险。凌晨4点多时,建军醒来,我本来想开一段时间车,此时,他有点不放心,还是爬起来继续前进。我怕他困,他满怀信心说没事。临赶到火焰山时,达军好像有精神了,接过车,6点多钟到达火焰山下,等日出。这个地方日出要8点,还有两个小时,大家在车上眯了两个小时。在阳光下,大家醒来时,都发现对方的脸色不好看。
的确,大家太困倦,没休息好,没精神,但当见到日出后的火焰山如此壮观时,都精神振奋,拿起相机各自寻找着拍摄点。火焰山自东而西,横亘在吐鲁番盆地中部,为天山支脉之一,形成于五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期。地壳横向运动时留下的无数条褶皱带和大自然的风蚀形成的火焰山起伏的山势和纵横的沟壑。在阳光的强烈照耀下,赤褐砂岩烁烁闪光。
阿里到扎达的路根本不叫路。一路上不知过了多少河,没桥,全靠冲水过去。路呢又全是搓板路,车速根本没办法加快,再说还要爱护车,车如果在路上坏了,几百公里无人那就麻烦了。
走旧公路要100多公里,但是要翻两个大坂,的确够人害怕。这路我不敢驾驶,停下车叫建军来驾驶。路窄不说,全是烂路,还是斜坡路,翻山不见顶,过一道弯,翻一座山,叫人出大把汗。
车不停地使用加力档,吃力地在蜿蜒的山路中盘旋。翻第二道大坂时,天色突变,下起了大雪。已是下午8点多了,建军不想开车了,王达军又接过了方向盘。下山时,他格外紧张。真他妈的比川藏路还烂,这哪叫路啊。
休息时,吃了个西瓜,干粮。实在太饿了,中午那顿稀饭哪能顶得住呢。建军说“肚子的奶油都没了”,达军说“最近严重缺营养”。在高原海拔5000多米的路上,我们三人的心都发慌。
当下山时,雨雪停了,前方看见光线。大家估计会遇上特别的光线,停下来准备拍摄。不一会,果然光线从云彩中射出,大家急忙拿出相机拍摄光影中的雪山。等了一下不够理想,又重新发动车辆继续赶路。车刚下到沟里准备上坡时,突然发现二道彩虹,特别醒目。我们催建军加速冲上坡,好取景。开足了马力,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山头时,彩虹也退了。大伙儿好一阵遗憾。
进入扎达的三岔口分道时,天色慢慢地黑下来了。这里的夜是晚上10点半左右。分道后我们是顺着一条河沟驶向扎达。这里本来有路,可是常年河沟的路被水冲洗,自然就没有路了。加上夜间行车,一会儿就不知道跑到哪条道上去了。基本上是顺着水流的河沟瞎开!
最烂的路还是建军在开,当过一个沟翻一个坎时,两次挂上加力挡,车都歪到很危险的地步,有翻车的可能,不敢再翻了,干脆顺着泥泞的河走。建军出汗了,在河泥里走怕把车陷入泥中,那就没办法了。大家都没走过这种路,建军一急“今晚只有拼了”。开足了马力,在河沟的泥泞中东倒西歪地向前爬行。我们的山鹿车很争气,又一次显示了它的越野性能。不知走了多久,总算是翻出了这条可怕的沟。
当翻上一个坡时,已近半夜1点多钟了,又不知道到扎达的路。继续开吧,大家开玩笑说,不要开到印度去了。这里离国界线已经不远了。达军太困了,几次提出“别走了,今晚就在车上过夜,明天早上再说”,建军坚持要开到扎达县城。
退回来找了一下路,心里没数。看地图也觉该到了,还是往前走吧,沿着河走。当看见一个桥和几个亮着灯的房子,这才心里有数了。
到扎达县已经两点钟了,到武装部叫开了门时,达军已睡着了,走进房子睡觉都不愿意,说了一声“我就睡车上算了”。我和建军什么东西也没拿,进了房子,顾不上室内的藏味,倒上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睡到早上10点,醒来时见窗外阳光很好,照在群山上,群山常年风化,显得特别壮观......有名的“古格王国遗址”就在扎达县境内20公里处......
—4—
高原的路很烂,开车非常危险。建军开得最多,达军也开,我也开,在云南那趟我把车学会了,这也算五万里行收获之一吧。当然,除了采访任务外,这趟下来收获最大的还是风光片子。风光还是靠一早一晚。很多拍摄点都是自己探出来的,要出一个好的风光片很难,有时十天八天也没一个好天。当时还没有从地理地貌啊这些方面去系列反映的概念,是拍多了积累下来慢慢有了思考。开始都没想系列反映中国西部风光问题,总是从景点上,往那里赶,路上遇到光影好的就拍。也没有想出画册,就是想展览,参赛,获奖。当时这就是摄影的出路,再有就是杂志刊登。
回来后,我说要把三军的名号打出去,做影展啊闹一下,对五万里也有个交代。但后来一忙就各干各的了,也没这个精力和经费,影展什么的也没办,但每个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都获了不少奖。
五万里行之后确实风光摄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部回来后,很多奖也就出来了,因为大家一看,很新,从地理从光线都很新。再后来又去几次,就找不到那个感觉了。当时的新鲜感、光线感就不一样了。有些地方反复去了好多次。我从小学美术,构图光影很敏感,一旦拍了风光还是有一定基础的。没有从地理的角度拍,是从审美的角度拍的。回来后画报刊登了边防报道,也刊登了一些风光作品,结合了哨所,使专题生动。1990年,我40岁,精力最旺盛的时候。90年代靠这些片子一年二三十个奖,风光占了不少比例。当时我获得的奖金最高的奖是广东的一个万元奖,一组四张西部片,就是土林、阿里......第一个万元奖。
回来后,我实际上也很苦闷,把万里行的片子拿出来看,疑惑这样的风光到底行不行。记得曾经有人到美国去,我整理了30张图片,让人家带到美国去请外面的人看看。就是想,都拍过了,怎么才能提升。后来人家跟我说我这个风光太讲究光影效果了,读不出什么东西。用光是摄影最基础的东西,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对你拍摄对象的理解。后来想想,我们遇到过很多地理地貌的东西非常感人,石头、树的结构和大自然的关系啊,但当时是不注意的。再后来我去拍,就是去抓拍自己心里对事物的理解,而不是寻找一早一晚了。我现在拍得比较写意一些,上一届全国影展又获金奖,把风光的因素加进印象的东西,最高的境界是印象,不是写实,这也是别人重复不了的。中国的风光也该改变一下,并不一定都要拍很美的那种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