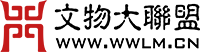王达军,时任成都军区后勤政治部摄影干事,《解放军画报》特约记者,37岁;
拍摄器材:两台尼康F3,一台玛米亚RB67。
(以下为王达军口述)
—1—
我1972年开始学摄影,一直在汽车部队跑高原,基本上是专职的搞新闻报道的干部。1988年我在成都军区后勤部,和解放军画报社与长城出版社搞了一本《西部奇路》的画册。那时候画册很少,出本画册不得了。我当编辑,片子大多是我的,内容是反映川藏公路上汽车部队的工作、生活。西部奇路就是川藏线,全长2000多公里,从修这条路的时候就充满困难、危险,每一公里就有一个烈士的英魂。几千公里全是土路,很多路非常危险,那时候没有火车,而我们的汽车部队要保障东线(昌都军区)进藏的全部物资,这里面可报道的故事非常多。这条路虽然艰苦,但自然风光非常美,沿路的民俗风情也很突出。所以《西部奇路》的画册里除了反映汽车部队的图片,也有沿途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民情。通过编这个画册,我对西部风光有了最初的认识。
画册出来以后,解放军画报社看了,觉得这个内容非常好,决定搞《西部奇路》连载。当时能上《解放军画报》也是很难的事情。1989年,军画报派袁学军来,那时他在军画报已经是有名的摄影记者了,我和他一起合作在半年中跑了三次川藏线,在画报上连载了6期。这次我们发现这种带任务的拍摄实在是太好了,到哪里都很方便,因为上面有总政,有《解放军画报》的牌子。我和学军就想着,今年做完了,明年能不能再做一次,再做一个大的活动?这次是川藏线,也走访了西藏边防部队。我们计划搞一个更大的,把西部跑完,那最少也要有五万公里,那我们就叫“西部五万里,边关采访”,要采访包括西部所有省区的边防部队。
计划有了,走西部五万里,走遍整个西部省区,谁来开车?我们不想找纯粹的驾驶员,因为以往我们在外面总是拍拍拍,看到好的随时就停车,经常拍到下午五六点太阳下去了才又开始赶路,如果纯驾驶员,他不喜欢这个就会觉得很没意思很累。所以我们想,能不能找一个他本身喜欢摄影,同时车又开得非常好的人。我马上就推荐了王建军。我和他一直是一个部队的,从一入伍,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他那时虽不是专职的,但我知道他非常喜爱摄影,而且他车开得实在是太好了,又能修车。后来建军和学军见了面,我们又具体策划这件事怎么做。往上打报告,三个人组成采访小组,报道西部,总政出文件,给《解放军画报》,给成都军区、兰州军区。
车是通过建军的关系找的成都军区后勤部队的一个汽车修理厂,他们做山鹿车,就是北京212改装的,装了轿子的壳儿,密封性就好多了。车还是不错的,性能比较稳定。找他们赞助,《解放军画报》也打了广告,车给我们用,车身上也喷上了“西部五万里,边关采访”。学军的一个朋友有个羽绒服厂,他们赞助了些羽绒服、睡袋,算户外装备。还有就是带一些压缩干粮之类的,修车基本工具,易损的汽车配件。每人还买了把麻醉手枪,防身。摄影器材方面,我是两台尼康F3,一台玛米亚RB67,那时专业单位用得最多的就是这个,现在看那个机器素质也不错。严格说我的条件最好,我在后勤那个地方,我们的领导,处长、政治部主任对我特别关照,我是有专门经费的,每年都有两三万块钱,这是专职摄影的优势。整个五万里行我拍了近300个反转片,主要是120,负片就更多了。学军在画报社也可以领一些,但不可能领几百个,不过负片黑白片他随便拍。建军就相对少一些,他那时候就是爱好摄影,不是专职的,可他非常好胜,路上就经常说:老子一定要超过你们两个人。
1990年4月4日,我们从成都出发。多数时候是建军开车,我坐在前面,经常会拿着地图,很多地方都没走过。边走边拍,行车过程就是拍片子的过程。到了某个兵站,进行部队的专题报道,这方面学军拍得是很到位的。我的精力主要拍风光,但我们当然是要把对战士的报道采访先拍完,虽然以学军为主,但我们的片子也提供给画报社。
1990年4月4日到11月,我们前后走了4次,分4段,走过了四川、云南、西藏、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新疆、青海,历时7个月,最后实际行程应该有7万多里。
—2—
在部队专职搞摄影,我的志向就是风光。为这个事儿,在五万里的路上,我还跟学军意见不同,有过争论。学军在车上说:“达军啊,风光意思不大啊。还是要拍社会,要拍人。”他1990年以前就是获奖专业户了,他认为风光片获奖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拍反映社会生活的纪实类的片子。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想法还是获奖。学军走到哪里,4×5的,120的,135的,反转黑白彩色,一个不落,都要拍下来。那时候在所有大的摄影比赛中,风光获大奖的,比如全国影展金牌之类的从来没有。可我说我就是爱拍风光,各有各的志向。我想我也不一定非要大奖,有小奖也不错。我还是喜欢风光,这是最能够表现我内心感受的方式。每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拍,而且,拍人我也拍不过他,总要走自己的长处。在那个时候,我们三人当中,我觉得我风光要强一些,就要坚持。当然那时肯定没想到会获什么大奖,1988年15届全国影展获的那个艺术风格奖我就觉得很好了,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影展,就上了8张片子,这在我们下边看来还是很可以的。那时全国影展在下面眼里还是高不可攀的。那次获奖对我拍风光是一个肯定,使我更加执着于这条路。当时我们在路上还自嘲,我说我是“风光大王”,学军说他是“人物大王”,这都是玩笑,自封的。
90年代以前,陆续也有一些国外的东西进来,像亚当斯、韦斯顿等人的作品,看了一些,有些连名字也没记住,有印象,但资料也不是太多。国内陈长芬很不错,还有何士尧、茹遂初他们的作品也看过一些。对我有影响的人还有李元,1989年进来的。还有阮义忠,经常写一些文章,介绍国外摄影。再有就是《大众摄影》、《中国摄影》,里面的每篇稿子我至少看三遍以上,那时也没有别的更多的东西,说那两本杂志是陪伴我们成长的良师益友一点都不过分。当获得《大众摄影》一个银牌奖的时候,我都兴奋了几天,人就是这样。大众摄影社还把我们请到北京领奖,那是1989年。这样的做法,给摄影人充分的荣誉,在当时确实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也是因为这些事,更让我对风光痴迷。
对风光,我就是喜欢,当时的拍摄没有什么约束,没有什么框框的。传统的风光摄影应该讲究情景交融,讲究意境,构图上前景、中景啊,非常考究,还有光影。但因为我没有更多的这种训练,就是按自己直白的感觉拍,拍自己感受的东西,而且西部风光本身带给我们的感觉那么强,也使我们会根据自己的感觉拍。西部的神秘就是我最想体现的,还有博大、空灵。
同时期拍西部风光的人很少,有新疆的赵承安,他没有获什么奖,但他对新疆风光的记录与展示做得非常好,有一席之地。还有于云天、李学亮,再有我们“三军”,我们算中国西部风光摄影最早的一批实践者。
—3—
西部五万里一路上也有一些历险吧,我是记不住故事的人,就记得,最险的路应该是从喀什到古格阿里。晚上在阿里无人区走河道,我们觉得应该上公路,上不去,最后车都立起来了,角度大概有60度了吧,险些翻了。要翻车就完了,真没办法了。不行又退下来,再走河道,走了很久才上了公路。半夜两三点了,我们心里发憷。我就说,我们要是看见印度国旗就赶快往回开啊,成偷渡了。开了一夜终于开到了。但到古格后,那种幸福是形容不了的,我们三个见到好的都是“哇哇”叫的。
走在路上,遇到绝色美景时,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赶路时有时又觉得自己是最孤独的人。有人开玩笑说你们一路上就三个小伙子在一起,又没个女孩,这一路上一定要犯错误。错误是没犯,太累。大量时间是行车中,最后跑了7万多里。沿途住兵站,有时住车上,有的时候赶路就连夜开车。到兵站也没机会给家里打电话,给家人爱人也就是写写信。但我爱人很厉害,她总能通过各种途径给我把电话打过来,能“追踪”我走到哪了,我到什么兵站了,她的电话就追来了。家人对我也非常理解,我走的时候我爱人刚好还受了重伤,但我已定好行程,就走了。现在想,太不对了。那时候一直在部队就是这样,家庭观念很弱,觉得就应该如此。她生小孩,我也不在,有任务。现在这些都是我的罪状。但当时部队教育非常正,就是以部队为重,家庭为辅,有点追求高大全的意思。但另一方面,像我们这样的人,你要说坏到什么地方也不可能了,脑子里还是充满那种积极向上的东西,现在还经常活在精神世界中。
西部五万里对我的人生,对我的摄影艺术是非常重大的历程。真正成就了我摄影后来的高度。对我们三个人都非常重要,对建军就是开了一条新路,因为他那时候本来都是政委了,算大官了,去了这次后,那条路他不要了,因为太喜欢摄影了。这也是冒了太大的险,这点我非常佩服他。
—4—
1990年前后,包括西部五万里行期间,直到我1993年转业,这是我的风光摄影的第一阶段:追光逐影。这也是成就我风光摄影的基础。那个时候还是讲求光影效果,当时这种追求光影的片子,有人说就是“黑乎乎”的那种。
1990年,我在16届全国影展获奖的《西部奇路》,就是“黑乎乎”的,蜿蜒的山路上,白色烟尘中,运输车队隐约可见,那个是我认为特别好的印象特别深的画面。我因为长期跑高原,跑川藏线,对路有观察,高原上的路很烂,特别是冬天,很干燥,车一跑,全是灰。车队前走后跟,后面的全是灰,什么也看不见。一天下来,战士们浑身上下就露两眼睛,这个情景印象太深了,就觉得一定要拍个反映路的这样的照片。元月,到了川藏线竹卡兵站,每年春节前,都有两个汽车连队专门去送过年的物资。我就跟着两个连队上去,沿途车队休整的时候,我下车。我跟车队说好了要拍这么个片子。车队又开拔,翻越觉巴山,30多公里的盘山道,我就先站在路边制高点,等车队,等山路几个弯道上都有了车,拍了这幅图片。风光摄影什么叫经典,有人说,不能重复的就是经典。这幅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算是我比较有体会的,是长期观察有了体会然后拍下的典型瞬间的画面。
还有一次是在青海湖鸟岛。那时候拍鸟岛,要不就拍那个岛,要不就拍那里的油菜花,特别精彩的片子在青海湖还没有。我当时想的我一定要拍一个真正与众不同的片子。那天我们在湖边时,大雨马上就来,乌云满头,突然有阳光从乌云的缝里照下来,一束光,下面很多鸟在飞。啊!心里太激动了。我拍了一幅《霞光》,画面上就一只鸟从亮光处飞过,恰到好处。这个看起来也是“黑乎乎”的,但那种神秘表现出来了。我当时非常激动,就是要抓这个。这个片子也是以后获金像奖片子里面的一张,现在看也是完全没办法重复的。
有人说拍风光是事先思考好的,这又有点蒙人,真正的拍摄即兴的特别多。当然里面一定有平时的积累,多看,多想,但具体抓的一瞬间一定是即兴的。一路上天气、光线让人心跟着起伏,看到好的真是激动,自然而然就激动,而且30年了,现在拍片子,我还是有那样的激动,只有那样的激动才能拍。人啊,运气也很重要,你一定要相信天意。比如1987年元月,建军才刚拿起相机不久,我们去海螺沟。在我们之前去的那拨人已经等了15天,天天阴天。我们元月4日去的,到了就晴,最好的光影,去了就拍了。当然,这也和准备和观察分不开。去一个地方前,要研究,天气可能会怎样,怎么走,何时走,这几天有什么变化,最后是运气,你遇到什么很难说。
“追光逐影”这段时间我成绩也非常好,因为那时西部确实没有什么人去过,没有那个条件,在这方面我们有优势。1993年前,仅西藏,我个人就跑了42趟,在当时绝对是最多的了。1990年,我们还在五万里跑的过程中,就听到我的《大地系列》获金奖了。1988年的15届全国影展的艺术类奖《喜马拉雅之光》,1990年的16届全国影展《大地系列》金奖,1992年的《西部风光》金像奖。同时,中日邦交20年,搞了“中日名家二十年”摄影展,都是名家大腕,高帆、吴印咸、简庆福、陈复礼、翁庭华、王苗等,还有我,我就算是最年轻最不知名的。正是西部五万里行之后,大家渐渐知道了我的西部风光。
—5—
西部五万里行回来后我们没有出画册,因为没有经济能力做这个。在王苗的《中国旅游画报》做过连载,在国内就完全没有做了。
1993年以后,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完成从专职摄影师到编辑的转变。这个阶段对我的启发更大。到画报社,副总编,总编,社长。条件没得说,都是最好的摄影器材,但思路变化了。做杂志要求方方面面,只拍风光片不行,也拍人文的东西,我对藏区风情、巴蜀地区的民俗比较关注,专门花很大精力去拍。但因为对风光的执着,这一块我肯定不会丢,不方便全国去跑去拍,我就立足西南,后来就完全是四川,专门做四川五个自然文化遗产。九寨沟、黄龙、峨眉山、青城山、都江堰、大熊猫栖息地。因为这些我能够把握,比如时间上,我可以周五晚上去,周日半夜回家,周一一早,9点开会,我准时出现在会议室。这些地方尽管大家都去拍,但我一定要把它拍到极致,让人完全无法超越。你可以去一次两次三次,但像我这样你可能达不到,我拥有大量的片子,反映每个地方的各种情景四季变化等等,而且技术层面片子的素质非常考究,大部分是4×5的反转片。可以说,这个阶段我追求的是高素质的片子。
后来我拍的片子,素质上技术上没得说,光影也一定是非常到位的,但公众视觉的东西多了一些,因为去拍的目的不同,拍九寨黄龙那些自然文化遗产,就是要表现那些地方,如果你按自己的个性拍得黑乎乎的谁看得明白是哪啊,既然是传播就要顾及公众视觉。我出了将近20本画册,全是文化专题,一本自己的画册都没出过。我的《四川藏地寺庙》画册在欧洲好几个书店都有。摄影它不光是艺术,更多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播。现在看,要是能把个性和公众视觉的东西再结合起来会更好,就会更丰富。
最近三四年,算我的一个新阶段,对黑白的重新认识。以前我暗房不错的,1980年还给人讲过课,我一直非常重视暗房,包括我获奖的片子,都是有后期制作的,这不是PS,但里面有调整,比如调光啊,深浅的变化啊,色调色彩的变化啊,等等,充分体现我自己要表达的一些东西,我发现黑白更有意思,这几年我比较关注黑白。我的风光摄影30年,主要就是这三个阶段。从追光逐影到对图片素质高品质的追求又到对黑白的探索,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