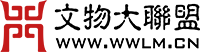王建军:时任成都军区体工大院政委,摄影爱好者,36岁。
王建军口述
—1—
1990年4月4日上午,成都军区机关广场毛主席像前,为西部五万里行举行简单的出发仪式。我记得很清楚,主席像的背后就是毛泽东的诗词——《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三军过后尽开颜”。出发当天,三人穿着军装。那时还没有“三军”的叫法,后来我们跑完了这个事以后,“三军”、“三军五万里”才这样叫起来。
我们走的中国西部五万里跨了两个军区,严格地说是三个军区:成都军区,包括云南、西藏、四川;兰州军区,包括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陕西;再有就是北京军区,只涉及一个内蒙古。活动叫“中国西部边关五万里采访”,这是喷在我们汽车上的名称。
活动主办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具体协办是成都军区和兰州军区,我们在部队,吃住行多数都有兵站接待,加油有油票,在部队油站加油,不要钱。顶多借些差旅费,当时钱的概念很少。1990年住个宾馆一二十块钱,住个招待所五六块钱,何况我们大部分时间是住部队。最终行程7万多里。开的是赞助的山鹿牌新车,用的越野轮胎,7个月跑下来,爆胎近20次,很多零件像刹车片、减震器、钢板、油箱都换过,最后发动机也换了。
五万里行之前我在成都军区文化部工作,对摄影就是爱好。我和王达军1973年到1975年都在兵站部宣传队,后来我们又同时分到了汽车团,我们又都在宣传队的乐团,他是拉二胡,我是吹长笛。那个时候达军就开始玩摄影,我没有,当时摄影还是比较奢侈的事。分到汽车团后我被分到4营去学开车,我喜欢开车,喜欢动,技术学得非常好。后来到1975年我被调到成都军区后勤部宣传队,1976年到1977年,又到四川音乐学院学习长笛,是工农兵大学生。1978年宣传队解散,我被分到后勤保卫处,搞保卫。1980年到泸州公安学院学习的痕迹检验,在这个时候接触了刑事痕迹照相。1988年调到成都军区文化部。1988年底到1990年我在老山负责整个战区的文化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拿起相机的机会就比较多了。1989年在老山前线、昆明、成都举办了《老山影展》。从学习公安拍痕迹照片算正式接触摄影,到1990年,对摄影只是爱好。
对五万里的活动,当时我想法很简单,我是业余的,他们是专业的,但我确实喜欢摄影,而且我这个人又好动,坐不住,跑惯了,有这个机会去转一圈有什么不好。我一直对新闻摄影报道摄影不感兴趣,因为都是摆出来的,做出来的,假的,有什么意思。我就喜欢拍我自己想拍的人啊,风光啊。三个凑在一块儿,兴趣相投,对我是个拍摄的好机会,同时学军也是著名的《解放军画报》的摄影记者,跟他们出去我也能从他们身上学些东西。后来出去几天,我发现摄影就这么回事,我就对学军、达军说:我会超越你们。

此次活动拍摄任务是有的,拍摄边防哨所。比如到了某军区,首先是让被采访的军区给我们提供拍摄线索,军区司令就会叫军区的相关人员向我们介绍情况。我们根据军区人员提供的线索,制订我们的拍摄计划、未来几天的行程。除了每个当地的采访任务,总政也有一些必须完成的采访任务。采访的稿件发表在《解放军画报》上。至于我个人的拍风光的计划是没有的。拍风光对于此次采访来讲应该属于搂草打兔子,就是觉得好玩,没有想过要拍到什么,也没有想去参赛,没这个欲望。就想出来走走,拍拍片,在艺术上技术上能有些提高。
对当时的风光摄影我看的也不多。知道有于云天,有组片子叫《九歌》,里面有张片子就是古格王国,叫《钟声》。我说过我是看着《日月》,听着《钟声》走上摄影道路的。《日月》就是陈长芬的。对风光摄影有兴趣,感觉到风光的内涵,东方哲学的审美,这点上陈长芬对我有影响。还有就是李元,1980年代,第一次把西方东方相结合的风光带到中国,他的东西很有韵律。再一个就是陈复礼,画意摄影,中国的意境的东西,对当时的我还是有启发。
西部当时很闭塞,极少人去,说句夸张些的话,把三脚架一支,相机快门一按,随便一张拿回来都能获奖,没人见过啊。曾经在论文里我写:站在领奖台上我感到茫然,摄影究竟是一种悟性还是一种缘分,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摄影如此简单——是我当时写的。学军、达军他们都是专业的,和他们一起拍,为了不重复,我当时拍摄算是有一个捷径吧,就是你用20广角拍的时候,我就用15的广角,你用200毫米,我用300毫米,你蹲着拍,我就趴地上,你站梯子上,我爬树上,同样的地方,拍的东西跟你就是不一样。达军看了曾开玩笑:狗日的,太聪明了。
我的摄影设备是自己的,佳能,当时是佳能最顶级的,F1、A-1、T90,镜头是齐的。胶卷上给我们赞助最多的是王苗,每人赞助了我们15卷反转片。拍完就收走。当时我们50多块钱的工资,一个反转片六七块钱。自己的胶卷自己解决,他们两个的渠道比我好一些。我要靠自己去化缘,公家也给我解决一点。因为胶卷限制的原因,那时候一年拍的量还不如现在一天拍的。7个月才拍了15个卷,反转片。现在我在飞机上拉萨航行一个来回就是50卷。
那时候也是见什么拍什么,但有一点,要拍好看的风光,我们认为好看的。第二个是稀罕的,比如这个光线难得等等。就是比较唯美的。在画面经营上,总是按照一个所谓的摄影构图来拍摄。摄影本身对光线要求就很高,我们所说的光线是适合中国西部的光线,日出日落啊,耶稣光啊,点光啊,我们当然很期待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我正好处于学习阶段,对光线特别注重。比如珠峰最后一抹光照在峰顶,一抹红色,确实漂亮。有人说中国风光摄影师就是一早一晚会拍,其他都不拍,但最开始那确实是拍摄中国西部的最起码的条件。到后来当然是很多天气情况都能拍。我觉得从学习的角度,那个阶段我们对光线的依赖是非常刻意的。
有些地方是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人拍,但应该回避“发现”这个词,就像很多登山家说的:山就在那儿。由于摄影师的先入先到,拍下了这些影像,使得后来去的人更多了。比如元阳梯田,确实是因为我们拍了之后出名的,后来我还成为红河州元阳的荣誉市民。因为当时摄影是特别奢侈的一件事,只有专业的人才有机会有条件拍。再比如红土地,珠峰,海螺沟,西藏的岗巴古堡、江孜古堡、纳木错等等,我们拍完以后,很多人跟着去拍。海螺沟景区还曾经要立一个牌子——王建军拍摄点,我赶快拦住了,这不是找骂吗。那时遇到的同行、摄影人极少。记得就云南泼水节遇到过,新疆遇到过李振盛、朱公(宪民),真正到青藏高原就几乎没有了,所以使得我们的很多片子独一无二。
现在去这些地方已经非常容易,不过肯定和20多年前不同了。比如珠峰,现在已经修了宾馆了,在我们当年的一些角度就不可能再拍了;再比如我们四川的米亚罗,因为修小水电站,公路的改建,当年那种迷人的红叶,现在已经荡然无存。纳木错,我们在纳木错拍的美丽的湖岸线,现在没有了,人太多了,已被踩得完全没有了原来的韵律。再有元阳,有些点已经修上观景平台了。在中国这些因为摄影而热的点也逐渐发生变化,有的甚至消失。
—3—
我认为去西部拍片,相机就是眼睛,汽车就是腿。尤其在中国西部,离开了车,相当困难。汽车是我弄来的,我和部队造车的工厂比较熟,厂里也想通过我们宣传车。《解放军画报》也刊登了车的广告。因为我有在部队当汽车兵的经历,长期在部队受整齐划一的训练,这种习惯也带到了五万里的行程中。我们的车干净得很,仪表台上容不得一点儿沙子。有时我们“三军”上车都是把鞋脱了,穿车上的凉鞋,谁把车弄脏了我都不高兴。修车工具不能少,千斤顶,易损件,像减震器、钢板胶套、发电机、油泵、备胎,还有胎的内胆都要带着,还有补胎的工具,这些全都用上了。
一般是我开车,旁边的人看地图。聊天都是和采访摄影有关的事,当然偶尔也说个黄段子什么的。车上装着暖水壶,压缩饼干,方便面。车里有磁带,放得最多的是阎维文的歌,《说句心里话》、《小白杨》。身上穿着成都有个羽绒服厂商赞助我们的羽绒服,下面瘦腿裤,现在看很可笑。当时穿惯了军装,肥肥大大的,猛一穿这个,本来人就瘦,跟瘦腿鸡一样。脚上,我就穿一双回力鞋,白色的,20元一双已经算很贵的了。
那时在国产越野车里,这台山鹿车算是不错的,底盘是北京212的,发动机是沈阳的,在国产车里算很稳定的,在路上几乎没出什么大事。最危险的一次是从喀什出发去采访神仙湾哨所,这是我们全军海拔最高的哨所。在昆仑山冰大坂上,我们被对面刹车失灵的一辆地方上的车撞了,躲都躲不开,我们已经靠得最边了,但那辆车停不住了。撞了,好在大梁没变形,就把壳子撞烂了。看到没大事,我们继续开,但没注意因为这个把发动机的螺丝弄松了。那时达军在开,开着开着听声音不对,赶快停车,瓦烧了,机油漏光了。停的地点前后都没人烟,也没有车辆经过。幸好我们在阿克苏的时候,人家团参谋长让我们带了台手摇电话机(有图片),说你们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就爬到电线杆儿上,接上线,摇。我身体最好我在最下面,他们两个在上面,那已经是海拔5000米了,骑在我身上,终于把电话接通了。电话里面说正好有个车在这条路上,应该快到了,让我们拦住他。不久真有一辆拉给养的车过来,拦下了。他们俩跟车走了,必须留下一个人在车上等。我一个人越等越害怕,天也黑了,旷野中,没人没车。为防不测,我又自己给自己自拍了很多照片,作为“遗照”。最后我把汽车上的备用机油倒出来,把螺丝拧紧......又慢慢把车发动,用最低速档,一步一步蹭到哨卡上,我刚到哨卡上就看到他们大车已经出来接我了。就那次还是觉得有点害怕。
这一路7万多里跑下来,确实累。记得一次返回成都,翻秦岭,都是土路,是一天一夜,开过来,开到成都已经累得不行了。回来见到我爱人我都没什么“性”趣了,我爱人还说“你们把王建军怎么整的啊,回来性欲都没了”。那确确实实是太累了。
—4—
西部的路是最险的,也是最美的,因为最险,也是最神奇的路。关于路上的艰难啊,劳累啊,车的瓦烧了啊,等等这些真不是事儿,因为在这之前我本身就在汽车部队,这条路上的险,生与死,我见得太多了。真正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近距离地体会到中国西部如此壮丽的自然景观,如此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初学摄影者也好,作为一个军人也好,作为一个旅游者也好,能这么系统地走完西部,这一路上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印象最深的。我看很多东西是过目不忘的,这西部让人不忘的不是说某一地的景象,对我来说是一个整体的西部,是一个丰满、有生命力的整体,它也不是拍几幅片子就能表现与概括的。最后回来我兵都不当了,要去搞摄影拍中国西部。
1995年,我转业。1990年的时候,三个人里我“官”最大,王达军那时是副团级的摄影干事,我是政委了,正团级。西部五万里行对我算个起点,萌芽,是我中国西部风光拍摄的开始,同时萌芽出离开部队走职业摄影师道路的想法,真正质的飞跃应该是转业真正成为职业摄影师后。那时无论从器材还是从拍摄理念感觉整个都不一样了。从1995年后到2003年以前,这段时间的拍摄才奠定了我西部风光的基底。而且西部风光热真正开始于西部大开发,并不是起于1990年。那只是个起点,对“三军”来说也是个起点。
对风光,从非常感性的层面,逐渐走向思考,走向理性的阶段,起码我在想了。技术上应该说是更熟练了。从这个以后,我确实做了一个痛苦的选择,这个选择不仅是因为西部风光这一点,而是因为我对整个中国西部的感悟,从不认识到认识,从没有走进,到深入,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西部大开发的热潮。我想,如果要走一个职业摄影师的道路,我必须有所失,有失才有得。我下决心走职业道路,专心致志去拍中国西部自然景观。
作为一个职业摄影师应该有一定社会责任,还要有为更多民众服务之心。我们如何用自己的劳动为没去过西部,没去过中国的人来展示我们的中国西部,这是我要做的。后来我带团,办旅行社都是为了养活自己来支撑我的摄影,并不是为了赚钱。职业摄影师就是要靠摄影来养活自己,走到今天我坚守了这一点。像是这样单纯靠风光摄影来养活自己的人在中国没有几个。现在我旅行社不干了,因为已经过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可以靠我的摄影得到回报,我还是要集中精力拍自己的东西。
我用中国西部守望者来定义我自己。一是我就守着中国西部拍摄,这是我一生的主要拍摄方向;二是要成系列成专题整体反映西部。摄影不光是追求美的东西,不仅要从摄影的角度看西部,更要从人文关怀的角度看西部,在世界的层面来看中国西部。1995年转业后,到2002年,我拍了大量中国西部风光,现在业界用的比较多的图片都是在这个期间拍摄的。2002年我出了我的第一本中国西部风光画册。到各地讲座的时候,我有两组图片,一是山远水远,自然风光,二是天地之间,人文风光。那时候在全国确实有很大影响,很多发烧友看了幻灯找我。所以我和陈长芬在1997年办了第一次走进西部的摄影学习班。后来这种班就很多了。对西部风光在中国形成那么大的影响,五万里是起点。
—5—
拍摄美国西部从2009年开始。一是拍中国西部那么多年,需要在观念上、技术上有些新的想法和突破;二是想看一下美国西部和中国西部到底有哪些相同哪些不同;三是想和美国的摄影家做一个交流,看一下在东西方不同的哲学观下对自然的认识理解;四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摄影师,我们的摄影语言具备不具备国际性。所以从2009年,我连续去了10次美国,去了他们西部最著名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也和美国的摄影家做了面对面的交流,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室,包括他们的生存状态,技术的运用,对自然的理解。
最近2012年这届金像奖,我就用了中国西部和美国西部两组图片参赛,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一下就获奖了。洪荒说得简单点就是地球初始的状态,说得科学点就是冰河时期形成的地理样貌。这不就是中国西部吗。在美国西部看的也都是洪荒之象。关于这个的论文我一天就写出来了,《关于风光摄影的思考与探索》。在美国西部拍摄时期,这时在思想上有个飞跃,从原来的单纯创作的思维走向文化层面的思考。从中国西部走向美国西部,再从美国西部回来,对我个人是一个飞跃。至少我的想法在我的摄影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从1992年西部五万里回来后获金像奖提名,到2012年的金像奖,这两个奖杯正好跨越了这20年,前面那个只是一个朦胧的、运气的,而后面的这个是扎扎实实的结果,是对20年前所作的那个选择的延续,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20后年自己更成熟了,是观念思想上的成熟。20年一瞬,在这之后应该又是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不是以这个金像奖为界定的,我想20年后应该更好。不管是形式上的东西,还是我们的想法,应该还要上一层楼。我今年59,到79可能拍的东西又不同。也许那时候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我想肯定会不一样。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国西部的守望者。没有当时“三军”西部五万里就没有现在走上职业道路的结果,就没有对中国西部全方位的认识,也没有对中国西部做个守望者的决心。